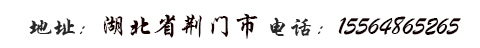那一年,沿图们江旅行下
|
那一年,沿图们江旅行(下) 刘文军(好望角) 防川,鸡鸣三国之地 对我来说,年的长春会议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会后随部分专家沿图们江下游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会议主办方联系到一架部队的苏制图系列小飞机,由长春飞往延吉。这种飞机只有20几个座位,机上只有两个驾驶员和一个空姐。飞机起降不稳,航行中晃晃悠悠,发动机轰鸣声不绝于耳。我以前没坐过几次飞机,更不用说坐这种蚂蚱一般的小飞机了,一路上提心吊胆,直到飞机在延吉军用机场着了地,一颗悬着的心才放进了肚里。 延吉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鲜族风情十足。当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朝鲜屯,尝地道的朝鲜冷面,听《阿里郎》《红太阳照边疆》和《桔梗谣》,与村民手拉手,围着篝火跳欢快的鲜族舞蹈。那时候旅游业还没兴起,商业化气氛不浓,吃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直到今天,我一听到来自延边的“阿里郎组合”用三声部唱起这几首鲜族歌曲时,都会想起20多年前的这次延边之旅。 第二天一早,一行十几人乘车来到中朝边界的图们,先参观图们边境口岸,然后沿图们江畔的边防公路一路行驶,来到珲春,最后到达边境线上一个叫防川的小村子。由于路况十分糟糕,汽车一路上颠簸不停,让车上人吃尽苦头,但那时候,人人都被激情和梦想充盈着,有一位老专家在车上说:“为了图们江通航,就是走搓板路也值得。”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却是这些老专家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防川村是图们江中国段的终点,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有“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之称。登上附近山坡的瞭望台,可以远眺日本海。但用东北话说,眼巴眼望,就是走出不去。隔着铁丝网就是中俄分界处的“土字牌”,两个俄罗斯士兵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腿上横着长枪,不时朝我们这边儿瞟过来几眼。 作为一名中国人,看着发源于自己境内的河流从别人的领土上流向大海,自己却无权走出去,能不着急吗?一位从吉林省科委退休的老专家多年在图们江流域奔波,他站在“土字牌”旁朝日本海方向久久凝望,然后回过头来,说:“图们江出海权不恢复,我死不甘心,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里吧!” 土字牌立于光绪十二年(年),是图们江下游划界的一个重要地标,负责办理这一事务的是清廷官员吴大澂。吴大澂是苏州人,同治年间的进士,金石学家,先后在陕甘、吉林、广东、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等地任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省级交流干部。在吉林期间,他与吉林将军铭安一起,建立边防军队,修筑炮台,创建松花江和图们江水师营,同时设立招垦局,移民垦荒,推行实边政策,是开发东北边疆的功臣人物。 有一次,我去穆棱寻访中东铁路伊林老火车站旧址,在兴源镇偶然发现路边有一个指示牌,上书“吴大澂纪念馆”,于是兴冲冲赶了过去。这个纪念馆是当地人为纪念吴大澂在这一带兴边的功绩而设立的,可惜那一天纪念馆没有开放。但隔着玻璃窗可见正堂有一副对联:道秉中庸和平处事,家传孝弟安乐长年,横批:一卧沧江,落款:翁同龢。一个地方官,能由帝师给题词,可见此人威望之高。 旅行记忆 这次考察让我们了解了图们江流域的地理地貌和人文历史,同时也饱览了边境风光与风情,唯一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到了长白山脚下却没能上去。杨大使对上山很感兴趣,我也希望能借他的光上去看看天池。杨大使对自己的年龄和身体有紧迫感,他私底下对我说:“如果这次上不了山,可能我这辈子都上不去了。” 杨大使向主办方提出了上山的愿望,但主办方表示为难,理由是上山的路不好走,需要事先联系等等,杨大使听后没有再坚持。现在想来,杨大使是个以事业为重的人,不善于考虑个人利益,再加上他是外交官出身,说话比较委婉。如果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把上山作为参加会议的先决条件,主办方一定会做出安排的。据说现在举办会议请大人物光临都要付高昂的“出场费”,会后安排周边旅游更不在话下。杨大使的做法体现了老一辈人做人做事的风格,还有那个年代纯净的社会风气。 20多年后,我由于热衷户外活动,在一个金秋时节来到长白山脚下,沿着西坡的木栈道气喘吁吁爬到山顶。那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雪后初晴,大气磅礴的天池美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据说有人多次来都没能看见天池的真容。遗憾的是,杨大使于年以97岁的高龄过世,长白山天池成了他未竟的梦想。 这次图们江之行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图们江下游地处偏远,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一次很难,会议主办方将行程委托给长春的一家旅行社,这家旅行社又两次转托,如同工程项目一样,层层转包,结果可想而知。 到珲春的第一天,专家们经过一路颠簸,舟车劳顿,人困马乏,本想好好休整一下,放松放松,哪成想,开饭时,辣白菜、桔梗、萝卜条上起来没完,最后是一盆米饭,外加一盆大酱汤,整桌不见半点荤腥,专家们面面相觑,当着主人的面,又不好说什么。这时,带队的陈教授脸上挂不住了,叫来导游,大声质问:“怎么回事?”小导游很委屈地说:“你们的经费有限,到我们手里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安排。”老陈有苦说不出,只见他以东北人的血性一拍桌子,大声说:“上菜,费用我出!” 返回长春后,得知回程机票没有落实。一番争吵后,旅行社给我们买到由吉林市飞往北京的机票,这意味着我们要先坐汽车从长春市赶往吉林市,再乘机。那时候的路况很差,公里的路程耗费了小半天的时间。一路上,专家们抱怨不断,一位来自韩国的专家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图们江,也是最后一次。”来自《经济日报》的记者黄建纲愤愤不平:“这不行,我得反映一下。” 回到北京后,老黄写了一个“豆腐块”,登在《经济日报》头版,这下影响大了,据说吉林省政府领导看到后大为光火,要求追究责任。有关部门专程到报社解释、道歉,希望报社能想办法为他们消除影响,老黄建议他们可以写一个东西,登在报上。可能考虑面子或者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吉林方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年夏,应东北师大袁树人教授的邀请,我又一次来到长春,参加“中国东北-东北亚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并应邀作大会发言。会议地点还是南湖宾馆,会后主办方也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包括德大禽业公司,我明显感到这次会议组织得比上次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闻媒体的力量。 摘自刘文军游记《边缘旅行》(人民交通出版,年7月), 北京中医治白癜风医院白癜风怎样能治疗好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nchunzx.com/hcly/6180.html
- 上一篇文章: 11月5日6日天津中医药大学工程学院院
- 下一篇文章: 2016年长春中小学学区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