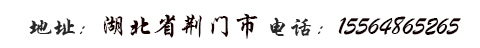从ldquo山贼rdquo到l
| 山东白癜风微信交流群 http://www.sinbg.com/fengshang/xinchao/675.html一二、招安手法两相同招安:《水浒》的重要话题招安是《水浒》中的重要话题,部分梁山好汉的“招安情结”,在未上山时已开始酝酿。小说第三十二回写杀惜在逃的宋江与亡命江湖的武松在孔家庄不期而遇,武松临到二龙山落草时对宋江说:“……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对此宋江深表赞同,说:“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此后,“招安”呼声在水泊中时有所闻。大聚义后,谋求招安更成为宋江苦苦追寻的政治出路。尽管这一方针受到部分好汉的激烈反对,宋江仍力排众议,身体力行。为此他亲赴东京,又不惜假“鸡鸣狗盗”之行,派遣柴进入宫侦察。并不避裙带之嫌,走李师师的门路,向统治者秋波暗递。乞降行动受挫后,宋江又张大军势,以武力相胁迫,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其目的,仍是“以斗争求团结”,以期见容于朝廷。经过艰苦的努力,宋江“全伙受招安”的夙愿,总算实现了。历史上的宋江结局也是接受招安,但情况却简单得多。宋江是在战斗失利、副帅被擒的情况下被迫投降的。尽管归顺后也曾受到封赏,风光一时,但整个过程与小说相比,差别甚大。那么,小说中关于招安的反复皴擦之笔,蓝本出自何处?事实上,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贯穿于洞庭起义始终。《水浒》的招安素材,无疑也来自洞庭湖。招安:同样是对付洞庭军的手段对民间反抗武装采取剿抚并举的手段,是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面对十分棘手的洞庭起义,统治者当然不忘在镇压的同时祭起招抚法宝。见于文献记载的招抚活动,先后有二十余次。李纲、程昌、折彦质、王、程千秋、张浚、岳飞等,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剿抚并重的策略。李纲的招抚成果,见诸前述。他是经略荆湖的官员中最早主张实行招安的。王也积极主张剿抚兼施,在卖力镇压的同时,向朝廷申请“招安金字牌”,并得到朝廷所赐“黄榜十道”[1]。为了分化义军,朝廷还“别给旗榜”,令王对起义军中的“西北无归之人”另眼看待[2]。此外,程昌、折彦质等地方军事长官也都尝试过招抚手段,然而效果均不甚理想[3]。张浚是招安政策的积极主张者和执行人。他和高宗曾就招安问题进行了讨论:(绍兴四年三月)丙辰,上问执政(即张浚——引者)湖寇事宜,张浚曰:“村民无知,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以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上曰:“皆朕赤子,何事于杀?然自军兴,盗起率招来之,而奸人乘衅,所在啸聚,今幸衰息,勿复效尤可也。”[4]这番对话,反映了最高统治者的忧虑。高宗唯恐招安策略会带来负面效应,使盗贼受到鼓励,“所在啸聚”,愈招愈多。高宗的这一忧虑,在他发给王旗榜时,也有所表示。《建炎》卷六六记载:请招安金字牌,上曰:“近来盗贼踵起,盖黄潜善专务招安,而无弭盗之术。高官厚禄,以待渠魁,是赏盗也。(杨)幺跳梁江湖,罪恶贯盈,故命讨之,何招安为?但令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尽管高宗对臣下的镇压效率深感不满,对招安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忧心忡忡,但仍不得不依从王、张浚等人的请求,不断颁发金字牌及旗榜,默许招抚手段的广泛施用。此后,高宗还“赐荆襄制置使岳飞金字牌旗榜十副,充招安使用”[5];这同样是依岳飞之请而颁发的。军事压迫与招抚利诱相辅相成,确实对义军联盟起到分化瓦解作用。义军头目杨华、黄佐、杨钦等先后投降,都立即受到封赏。最早投降的杨华被程昌?任命为抚州钤辖,又于绍兴四年“特补修武郎,添差临安府兵马都监”[6]。黄佐则被岳飞“擢佐武义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后又转为武经大夫。[7]杨钦投降的当日,岳飞便将朝廷颁发的“空名武义大夫告书”填写给付,然后再向朝廷奏报[8]。然而招抚政策并非对每位起义领袖都起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官府派去的招抚使臣不是碰壁而回,便是遭到杀戮。岳珂《金佗粹编》卷六《行实编年》卷三谓岳飞遣使者招谕义军时,回顾说:先是,鼎州太守程昌?遣刘醇,荆湖南北宣抚使孟庾遣朱实,湖广宣抚使李纲遣朱询,荆南镇抚使解潜遣史安,湖南及诸军遣晁遇十七人,邵州太守和璟亦累遣人招安,皆为贼所杀……然而统治者并不死心,对起义中坚分子杨幺、黄诚等开出高价,重利诱惑;甚至由高宗下诏,许诺杨、黄投降后,可授予知州的高位。《建炎》卷八五谓:(绍兴五年二月)……诏黄诚、杨太等如率众出首,当议与湖南、湖北知州差遣。先是,张浚以湖寇为腹心害,欲招来之。会诚之党周伦,自称统管乡社水陆兵马,以状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钟相作乱事归罪于孔彦舟。诏以黄榜放罪,令诚等一行人船,趁此春水,顺流赴张浚行府,或刘光世军前,当议优与转官,仍旧专充水军。若有愿乞外任之人,许乞本乡或邻近州军钤辖都监差遣。愿归农人,于鼎、澧州支拨闲田养赡,仍免五年税役。伦又言:“刘豫遣来招诱使臣前后十人,已行斩首,乞下边界几察。”诏诚等忠节显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飞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不管周伦所作的效忠姿态是否能代表杨幺,实际结果是,杨幺、黄诚(甚至包括周伦)面对如此优厚的招抚条件,仍未动摇其最初信念,表现出矢志不渝的反抗立场。洞庭湖招安、反招安的斗争,留下大量文字记载和口碑传闻。《水浒》作者在创作招安情节时,有大量素材可供选择。事实证明,小说作者笔下曲折的招安故事,正是对洞庭素材拣选提炼、吸纳创写的结果。小说与历史,招安曲折多《水浒》中的招安过程,经历了三次起伏。第一次在第七十四、七十五回,写朝廷因讨伐梁山不利,于是改剿为抚,由御史大夫崔靖提出招安方案,委派殿前太尉陈宗善前往招抚。然而阮小七等偷喝御酒、凿漏天使船只,加之诏书口吻傲慢,蔡京、高俅的两个爪牙张干办、李虞候又狂傲无礼,这一切大大激怒了水泊英雄,几乎酿成一场大乱。多亏宋江百般回护,陈太尉仅以身免。第二次招安风波发生在第七十九、八十回高俅亲征之时。此节写宋江等通过被俘军官韩存保谋求招安,得到朝廷应允。然而高俅听从济州老吏王瑾的毒计,将诏书中“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的文句,破读为“除宋江;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并与赦免”。梁山好汉当场识破诡计,将天使射死,一哄而去。第三次是在三败高俅之后,宋江再派戴宗、燕青等走李师师门路,面见天子,倾诉衷情;又得宿太尉之助,终于求得一纸诏书,梁山泊至此才“全伙受招安”。纵观小说所描写的招安过程,与洞庭史料多有重合。如在小说中,朝廷内部对待招安一事始终主张不一、举棋不定。起义军内部对此也有态度不同:宋江的热衷痴迷,柴进、燕青、戴宗的奔走操作,李逵、三阮、鲁智深、武松等的极力反对,都可在洞庭史料中找到根据。招安经历多次反复,双方各怀机心,互不信任,招安使者也往往因此送命,这些地方,与史实也多有雷同。更有一些细节描写,如谓不是出于因袭,则无法作别种解释。如第八十回读破诏书一节,虽出于小人诡计,看似偶然,体现的刚好是统治者的本意。《建炎》卷六六载高宗对王招安请求的训示,谓:“‘……但令破贼后,止戮渠魁数人,贷其余可也。’乃给黄榜十道:‘自幺及黄诚、刘衡、周纶、皮真并近上知名头领不赦外,胁从之人,一切不问。’”这里的“自幺……并近上知名头领不赦外”的句式,与“除宋江”的句式,几乎相同。小说中的某些场景,也有着洞庭历史的影子。《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高俅拥天使在济州城头宣读招安诏书,梁山军马齐至城下听诏。宋江在马上欠身,与城上高俅声喏应答。当听出诏书中破绽后,梁山军马放箭射死使者,然后“一声鼓响,一齐上马便走……自回梁山泊去了”。这样的场景,同样见于洞庭史料。据《建炎》卷三九记载:(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寅)水贼杨华等乘船至鼎州城下,声言乞招安。镇抚使程昌?遣孔目官刘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贼断其首,鼓枻而去。这种城下之盟的招安场面,应当就是小说中“城下听诏”的素材原型:一方表示愿受招安,另一方则持檄相招;双方的接洽地点,又都在城垣之下。最终则谈判不成,义军杀招安使者而去。若没有真实历史记录的启发,小说作者很难闭门造车、凭空想象,作出如此具体的场景描画。杨华是洞庭湖中最早接受官府招安的义军头领之一,属于义军中的“动摇分子”。但他的投降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从主动谋求、到谈判不成杀戮使者、直至投降受封的曲折过程。从杨华出尔反尔、犹豫再三的行止,正可体会宋江等小说人物的复杂心态。杨华的背叛行为,引起义军中坚人物的反对和斥责。据《杨幺事迹》叙述:杨华本是税户,颇晓事体,即随李珪来城中参拜,程吏部厚以犒劳,令杨华亲随人回水寨,遍谕杨幺等诸首领,各请出来受犒。讵杨幺等不听,却极口骂杨华不是丈夫汉,遂鼓率贼舡无数,时来城下叫喊,声言要取杨华归寨。程吏部已得杨华,拘留监管,具事理申奏朝廷,承指挥差人管押杨华赴行在,蒙命之以官,差充抚州钤辖,不厘务。观照小说,与宋江谋求招安的一意孤行相对立,《水浒》作者也着意描画了阮小七的恼怒、李逵的斥骂、众英雄的反感牢骚……这一切,又都可以看作洞庭英雄反对招安、斥责叛徒的历史回声。注释[1]《建炎》卷六六。[2]《宋会要辑稿》“兵”十“讨叛四·杨幺”。[3]《中兴小纪》卷一六载绍兴四年程昌、折彦质等招安情况:“程昌乃募人能引随者,与获级同。故降者稍众,遂申朝廷,乞招安。时知枢密张浚自蜀还,留其属官冯楫,同湖南帅臣折彦质措置招安。丙戌,宰执奏其事。上曰:‘幺等凭民啸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折彦质招之,以成朕好生恶杀之意。’既而行下招安,而贼以不堪昌杀戮为辞。寻有诏,除昌徽猷阁待制,知镇江府,候招安毕日行。”又同年六月己亥,“先是,荆南制置使王自鄂回鼎,奏已招到贼众万余,然贼累杀招安使臣晁遇等,且乞割州县如溪洞故事。是月,湖南帅折彦质报贼不可招,乃复遣兵蹂践贼禾。贼乘大水攻鼎州社木寨,破之,官军死者不知其数,贼愈增气。与镇抚使程昌,皆坐降官”。[4]《建炎》卷七四。[5]《建炎》卷八五。[6]关于杨华招安后受封职务,可参见《杨幺事迹》及《中兴圣政》卷一五记述。[7]宋岳珂《金佗粹编》卷五《行实编年》卷三。[8]宋岳珂《金佗粹编》卷一一《家集》卷一《招杨钦奏》;关于黄佐授官,同书《行实编年》卷三又说“授武经大夫”。一三、结局与善后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小说与洞庭史实的另一相似之处,是关于起义的善后工作。——按说这两次起义的结局截然不同:梁山好汉是接受招安,主动投降;洞庭义军则是军事失利,被迫缴械。然而从两场起义的善后情况,仍能见出二者间的映照关系。一场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武装起义一旦结束,其善后工作纷繁复杂,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对起义队伍的改编删汰,对周边民众的安抚恤助,对旧有军事设施的拆撤焚毁,都是当务之急。不过文学不同于历史,小说作者完全可以不顾史实,只拣自己和读者感兴趣的情节描述,把烦难枯燥的史实扔还给历史。但不幸的是,中国的小说家几乎个个染有“历史癖”,即便像《水浒》这样的英雄传奇小说,作者也总要向史书看齐,追求“无一字无来历”。当《水浒》作者从洞庭史料中选取了大量素材之后,自然不能不注意到起义的善后工作。而史乘笔记对洞庭起义结局的详细描述,又实属难得,这使得《水浒传》作者难以摆脱材料的诱惑,特意在小说中记录了“分金大买市”的特殊场面。《水浒传》写梁山好汉受招安之际,宋江先对队伍进行删汰整顿,谓众喽啰:“汝等军校,也有自来落草的,也有随众上山的,亦有军官失陷的,亦有掳掠来的。今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速上名进发。如不愿去的,就这里报名相辞,我自赍发你等下山,任从生理。”当下辞去三五千人,“宋江皆赏钱物赍发去了”(第八十二回)。宋江又吩咐张贴告示,周知附近州郡、四散村坊,宣布梁山“买市十日”。于是“发库内金珠、宝贝、彩缎、绫罗、纱绢等项,分散各头领并军校人员。另选一分,为上国进奉。其余堆集山寨,尽行招人买市十日”。山寨中对前来买市者酒食款待。“四方居民,担囊负笈,雾集云屯,俱至山寨。宋江传令,以一举十。俱各欢喜,拜谢下山。”(第八十二回)场面火爆,气氛热烈。在第八十三回中,作者还描写了梁山散放船只,拆毁屋宇及三关城垣、忠义堂等情况。岳飞呼喊:“勿杀,勿杀!”当年洞庭起义的善后工作,因官军统帅岳飞的格外宽大,少了许多血腥气。岳珂《金佗粹编·行实编年》卷三即记录了杨幺被杀、诸头领或擒或降后,岳飞与部将牛皋关于如何对待失败义军的一段对话:牛皋请曰:“此寇逋诛,罪不容数,劳民动众,亦且累年,若不略行剿杀,何以示军威?”先臣(指岳飞——引者)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于钟相妖巫之术,故相聚为奸;后乃沮于程吏部尽诛雪耻之意,故恐惧而不降。日往月来,养成元恶,其实但欲求全性命而已。今杨幺已被显诛,钟仪且死,其余皆国家赤子,苟徒杀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连声呼谓官军曰:“勿杀!勿杀!”牛皋敬服其言而退。善后工作随后有条不紊地展开。岳飞一方面委派了精干的官员,对义军成员拣选删汰,“命少壮有力者籍为军,老弱不堪役者,各给米粮,令归田”。结果自请归田者有二万七千余户,全都由官军发给凭据,遣归乡里。得数万强壮者充军,岳飞军力也益发壮大。岳飞“又命悉贼寨之物,尽散之诸军,而纵火焚寨,凡焚三十余所”。又“揭榜于青草、洞庭湖上。不数日,行旅之往来,居民之耕种,顿若无事之时然,湖湘悉平”[1]。《水浒传》第八十二、八十三回对梁山善后工作的描述,无疑来自洞庭史料。如对义军群众的发落,对寨中财物的处理,对寨栅等军事设施的拆除焚毁,以及张贴布告,周知郡县,人民欢悦等情景,都是洞庭义军善后工作中所特有的情境氛围。所不同者,洞庭义军虽然没有遭受过分残酷的报复,但毕竟是战败屈服。战士编入军籍,带有强迫的性质。而“悉贼寨之物,尽散之诸军”,也仅限于对官军的犒赏。《水浒》一改义军被征服的结局,宋江等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主动撤离山寨的。于是一切买市、善后之举,也便成为起义者的主动行为。在这番善后工作中,宋江的地位,实则等同于主持洞庭起义善后工作的官军统帅岳飞。——论者早就指出,《水浒》作者在塑造宋江形象时,有意吸收了岳飞的某些素材[2]。如果此言不错,那么将一位绿林英雄与一位官军统帅联系起来的,恐怕仍是洞庭起义这一历史事件。《水浒》作者对洞庭素材所表现出的依赖性及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注释[1]岳珂《金佗粹编》卷五《行实编年》卷三。[2]参看孙述宇《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年版。本章小结本章在第三节中提出梁山起义的八个特点,指出凡符合此八点者,当为小说故事的主要历史原型。从本书第四节始,共用十节的篇幅,考察了发生于南宋初年的洞庭湖农民大起义,并与小说情节作了逐条对比。首先,洞庭湖是一处水乡泽国,那里曾发生过中国历史上唯一一场以内陆湖泊为依托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义军依山傍水构筑起坚固的水寨,“水”是那场起义的生命线;《水浒传》所描绘的据水结寨的起义模式,舍此没有其他模型可以借鉴。——而历史上的宋江以陆战为主,甚至没有兵过梁山的记载。其次,洞庭起义声势浩大,战斗人员多达十万,这与小说的描写完全一致。义军中除了荆湖地区的土著百姓,还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无归之人”,形成“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特点。——这正是《水浒传》所描述的情景,远非历史上的宋江三十六人可比。第三,洞庭义军的基本群众以农夫。渔父为主,兼有市井豪侠、散兵游勇、乡绅文士。这也正是梁山队伍的构成成分。——历史上的宋江一伙,成分要单纯得多。第四,洞庭义军首领数以百计,最高领导层经历了由钟相到杨幺的重大更迭。这使我们得以明了:为什么小说中的山寨头领多达百人,而山寨之主经历了从晁盖到宋江的更替。——历史上的宋江始终是队伍的大头目,在他前面,并没有一位开山者。第五,洞庭起义旷日持久,长达五六年;又因占据南宋王朝的腹心之地,被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水浒传》中的梁山义军,也屡被统治者视为“腹心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声势规模远不及此,至多不过是“癣疥之疾”。第六,为了镇压洞庭起义,南宋王朝曾七易其帅,发动多次围剿,动用了水陆兵种,还在水战中使用了先进的车船。在这一点上,《水浒传》正是洞庭起义的翻版。——历史上的宋江采取游击战术,官军随处邀截,作战方式与此全然不同。第七,统治者对洞庭起义进行武力镇压时,还不忘以招抚手段软化反抗者的斗志,前后多次派使者进行招安活动;而招安恰恰是《水浒传》的重要主题之一。——也只有在招安这一点上,小说与历史上的宋江有所重叠;然而细节方面,小说又多取材于洞庭史料。第八,岳飞率领的官军在镇压洞庭起义及处理善后事宜时,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善后工作有条不紊,绝少血腥气味。小说中的义军善后处理,是这一独特历史场景的翻版。——这一场面,显然是历史上的真宋江所难以梦见的。前举八点,概括了起义的各个方面,而小说与洞庭史实竟完全吻合,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若说巧合,两点三点倘或有之,断无八个方面完全一致的道理。相反,拿小说中的描写与宋江起义史实相比,则八点中只有受招安一事还有一点影子。杨幺与宋江,哪一家是《水浒》素材的主要提供者,可谓不言自明。第二章吴读本:一部时空颠倒的古本《水浒》一四、吴从先读过古本《水浒》吴从先其人《水浒传》与历史上的洞庭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实经前文的论证检验,或可初步确立。然而洞庭起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长江流域,与小说中那场发生在北宋末年、黄河流域的农民起义相比,在时间、地点、历史背景上的差距不可谓不大。那么“水浒”故事的作者又是经过怎样的运作,将大量南方故事素材植入一部北方英雄传奇的?这种移植,是否有着某种过渡媒介?我们是否还能在现存的文字记录中,找到这种移植运作的痕迹?幸运的是,这种痕迹居然还能从笔记杂著、戏曲文本中找到一些;而明人吴从先的一篇《读水浒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存于今的早期《水浒》版本信息,弥足珍贵[1]。吴从先,字宁野,号小窗,延陵(今江苏常州)人,主要活动于明万历前后。他生平潦倒,寄情山水,有游侠之风。与当时名士焦竑、黄汝亨、冯梦祯、汤宾尹、陈继儒、何伟然等过从甚密。吴从先颇有文名,落笔“生鲜”“妙绝一时”(沈明龙《自纪序》),他的小品文,常能入选明清的小品、尺牍集。吴氏一生编撰文集四部,皆以“小窗”命名,分别是《小窗清纪》(五卷)、《小窗艳纪》(十四卷)、《小窗别纪》(四卷)和《小窗自纪》(四卷)。其中《小窗自纪》卷三刊有一篇《读水浒传》,为《水浒》研究者格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nchunzx.com/hcjj/16500.html
- 上一篇文章: 最贴心的韩食酒屋长假过完,优惠依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