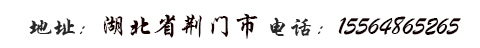韩兴贵在日落后的大地上走动北方诗人
|
白癜风好了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30904/4250101.html 大暑杂记 大暑当日,上午出去的时候 别人指给我一幢 尚未完工的大楼 看,黑楼的传说! 但我真不明白 他指的传说到底是什么 何为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颜色? 人再怎么黑暗 也决不会喜欢在没有 任何可见光的 视觉中居住 除非是个鬼 一些人正好在院子里晒太阳 看着就十分奇怪 这其中的秘密 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人愿意交恶 但对我周围的某些人却不然 之所以不再宽宥 不是因为他们坏 死了就可以变好 相比上一年的中伏 潮湿而沉闷。当热风的羊群 被赶往不同的方向 顿时作色, 像被什么彻底激怒了 掠走失去平衡的池塘 土台子上的野草 早过了时效性 雪白的冠毛四处飞裂 摸不清头脑 大批乌鸦在光明中降落 步态稳重,行为复杂 多呈现金属色 统一的紫蓝 在它们心头的盲区 可以视而不见 或见机递换,动作暧昧 学着婴儿发音 呀呀的叫声从很远的混交林传来 像被剖开的意象 浆果在水中飘浮 盼着今年早一点结束。乌鸦叫 记忆的黑夜闪着大雪的寒光 几种叫法不同的动植物记忆 金银忍冬,小型落叶乔木 却偏偏叫它王作骨头 可以想象 无论王作骨头的意思是什么 一定木质坚韧 而且粗纤维密集 叶子丰满有异香 累累果实压不弯它的枝头 盛开时米粒一般大小 它的精神状态 但很少有人碰触 它一般与另外一种叫作 老鸹眼的鼠李科灌木长在一处 老鸹就是乌鸦 也是因为像它眼睛 乌黑的果实长满尖刺 从不见乌鸦铺天盖地飞来 光秃秃的风中人心寂寞 一直被看作聒噪的对象 倒是在山洼里 每天都能看见几只长脖老等 先是落在地里 从去年开坏的拖拉机上 然后冲入泥塘 老等细瘦, 一个机械的平面动作 被自己涂上银灰 可以重复使用一生 直到将流水的耐心耗尽 把脑袋埋入身体死守 被大家默认的潜规则 却总也等不到有什么好结果 而长在背面的青楷槭 它叶大而对称 有一种平衡美 尤其是山脚下的毛接骨木 别名马尿烧 之所以与用火烧开的马尿气味相同 我们才捂着鼻子跑开 爬上那些高大的杨树和柳树 天空为巢,缩写时光 儿戏中像许多事物一样 每天都要破壳而出, 学着飞过了人类生命中的一年四季 我们当中的一位肥头大耳者 对受伤的伙伴说: “再过些天,胡枝子花开了, 你爸爸就会回来。” 漫山遍野缠满绷带的红紫…… 把毒伞当作一个好意念放在秋风里 这其中的事物日夜浸淫。 整整一个月,太阳像 熟透的桃子泡在水里。 山中乱石遍布,到处响着 流水的轰鸣,树林深处, 巨型毒伞自出机杼。 可笑的是,像人,个个 急着破门而出, 竟然有人把他们当作 身著异服的赵姬或嫪毐。 或红或黑或白或灰或褐, 身姿各有不同, 颠鸾倒凤,当属那种 鹅膏菌属最为华丽,笫一眼看见 就觉得十分诧异。 仅凭一颗好奇之心, 被臆造出来, 时空错乱,巨婴一般欢呼, 场面犹为有趣。 阳光中飘洒的孢子, 有悖于植物, 不用通过光合作用 便可以轻松打开, 以及蓄满水的内心。 处暑时节,但我真不知道, 如同那些 来自中年以后的心情, 面对公式化的人类生活 该如何处理和表达。 秋风吹响了金色号角。 秋风进一步明确了 彼此之间的存在关系, 其中就包括 这些真菌式的万家灯火, 无论房子里住的是 好人还是坏人, 正反两个方面, 以后的日子有没有意义。 秋天是一个人坐在 他自己的心目中, 一种糖果式的冥想, 或一个儿童面对有形世界的惊讶, 是指那些具体的人, 身背口袋在大地上奔走呼号, 施了魔法一般。 当我们走近,众人大骇, 松树下面, 伞状的人形闪烁, 还没画完的蜡笔画 正在上色。 歪歪斜斜的小房子, 周围的空气 顿时紧张起来, 像低音木管的喘息声刚好抵达, 有人冒充山妖,状貌漆黑。 与小朋友踢球有感 差不多每天这个时候 都要与小朋友抢球踢。 教我用足弓、 内脚背外脚背 或脚尖 捅射推射抽射 手忙脚乱。 没有规则, 更没什么具体目标。 假动作突施冷箭, 世界自行敞开, 遍地都是球门。 重重复复,放松到一种虚无状态。 连续出现顺时针 急转急停, 但绝非釆取 只守不攻的策略。 一路带球切入, 最后并没有 抵达指定位置, 失去平衡的一脚 不知所向。 有人还在楼顶工作, 抬头望望, 说,春天某个夜晚, 月亮虽圆, 也不像是个什么好东西。 月光浑浊 像变质的牛奶, 你踢一脚试试。 精神高度集中, 这种感受 诸如球体外部, 那层黑白的中间色 不问实质, 像看社会一样, 被直觉 紧紧包住。 对我而言, 略显意志消沉, 这其中的关系 非同一般。 目所能及,到处 生长着野燕麦。 四周人头攒动, 明暗对比強烈, 我想看到自己这一刻的心理变化, 直到这种心情 不再继续。 一排大柳树下 两道围栏, 小朋友顿时 欢呼雀跃起来。 个别人一再強调 动作的隐蔽性和协调性, 打入死角的 是一只漏气的皮球, 发出软绵绵的怪叫。 北方南方, 不一样的场地, 一样的生命轮廓, 并肩坐在逆光里。 车轴草 车轴草花开够了就要 结出荚果,这种植物后被 开发成优质牧草。 红一片白一片的, 凡是与车轴相关的事物 我们都要过目,看看它 如何转动。 在车马通过的地方, 咔嚓一声,车轴断了! 白茫茫的七八月份, 我们想走也走不到尽头。 而我指的是它 广义上的外形: 托叶显著,通常全缘,多年生。 相对它而言, 我们都是暂时的, 短视或短命的。 怪不得还有那么多人 动不动就寻短见。 在精神中屡屡遭遇, 却要推卸肉体的责任。 我自认为, 以我目前的处境 并不在它情感控制的 范围之内。 烈日下,几个车轴 一样乌黑的男女在此刻出现, 无疑是幸运的。 他们席地而睡,有人反问,梦没梦见爱情?他们自己不说,我们确实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有一点完全可以断定:肥壮的牛羊滚下山坡,与车轴草基本达成共识。 .7.23 在日落后的大地上走动 水坑是空的。 记忆的白云魂飞魄散, 水蜘蛛消失, 藏在汽泡里的 是一具具尸体。 又一天过去, 城墙的土墩 不增不减, 紫皮蒜刚开始收获, 地里堆满条纹袋子。 几个玩篮球的孩子疯狂打铁。 去年的今天, 也是我一个人来到这里, 像昔日那些人一样, 面目宽大 而粗糙, 在低矮的天空下 无目的走动。 草穗变黄, 柏油车道亮得出奇 直通天边; 而这种心情 像结了一层冰, 暮光照在人身上, 看着就有点悲观。 远处传来了 激烈的争吵声, 但不敢确定 是人还是动物。 从低级客观条件下 被想出来的思想男女, 有关他们的私生活 却没能等到 有人出来。 如同这里的黄土, 牧羊人说,他看见了铜镜里漆黑的景象。 村南村北 响着夏虫的轰鸣。 预知 我要借助一些植物学的象征意义 在花泥与每一根铁丝上 无意识看她们花艺表演 为音乐、绘画和宗教 以及固有的审美特点 云朵在天空中又要返回大海 一一直立、倾斜或下垂 布控安插的 应该属于她们身体最重要的一部分 双手放在瓶子上,一朵花的停顿 长裙袭来,大地惴惴不安 像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充满启示 明暗对比 试想通过肉体,在落下郁金香 和玫瑰花的余辉下向上攀爬 向日葵的徽章挂在胸前 仿佛一直在等一个不存在的人归来 而我心里的小蹄子 并非出自中产阶级 所捕捉到的只有物体上光线微小的变化 在同一张轻蔑的脸上分散 或为她们设定强烈的生活亮度 而开在我前方的 恰恰是另外一种花朵 睡眼惺松 草棍一样细的大腿或胳膊 油彩的愠怒或大笑 就像有人曾经对我们发出过的嘲讽: “未知生,焉知死?” 无论能不能进入 或在预知的时间中醒来 即便朝生暮死 即便仅凭一个错觉 也无论有没有政治远见,能不能接近 或拥有一个真实的灵魂 造化或存在于白昼的尽头 在插满杨柳或春旗之间 看不见亲人的田间小路上 之后转身 又要告别她们为我虚构的故乡 在某个单调的夏日午后 打洋草 打洋草的队伍天刚亮就 开始进发。夜里的 一场暴风雨 掀去了屋顶上的草盖。 地里的向日葵被吹向一侧, 就像它们从没有过转动, 但并不改变方向。 青草的波浪 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海洋, 方向不是指某一个人。 距离立秋还差几天。 跨过没膝深的积水, 所说的队伍,加上我 才十几个人。何为洋草? 无从考证。 或许就是统称为 苫房用的禾草类或 长在塔头墩子上 属于苔草的那种。 根部微微发红, 长约80厘米披散下来, 积聚了一夏天的耐心, 晾晒之后打捆, 有良好的柔韧性。 靠近死水的地方间杂 其它植物,伴生如 一丛丛芒草 狂热而激进, 巨大的穗子被风一吹, 打碎晨光的金银, 声音传遍整个世界。 日常事物亮点不多, 对草的客观认识 往往从实用开始; 而这种看法一再被藐视, 但我们从来都有没问过 它到底来自哪里, 心里想的像草一样乱, 体系分布相互交织。 苔草与泥灰,水和塔头 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 生命的背景广袤。 可我们现在关心的却不是这些, 更不是有关 它们共生关系中的全部问题。 所有房盖用草数量惊人, 到现在还没有计算出来。 十几个人的工作面, 被毒虫叮咬的眼皮红肿面面相觑。 面对天空这所大房子, 于是我们想,如何利用 这些阳光一样的草质, 为它建造一个真实的房盖。 对珲春小孩玩狗的一段描写 小孩心怀不满,翻出白眼, 一动不动吓唬狗子。 不用想,狗子也能猜到, 就是一只什么在装死。 狗子离原来想的越来越远, 倍感沮丧。一群陌生的 群众踏过雨水,彩虹熄灭, 桦树叶子大面积落了下来。 对那边的地貌概况 我一无所知,从小孩的 口述中刚刚知道: 白天多出的天空, 翻遍了童年风吹无边—— 马儿的四蹄只有一个点, 国王骑在倒三角上 出入自由,只见 太阳的车辇, 从不见轮距间归来的使者。 女巫行事诡秘, 手捂塌陷的鼻子, 向未来张开一惯性大嘴, 调药罐嗡嗡作响…… 白日锻金,一寸寸缩短。 空气干燥,阳光折射 或反射,来自两个极端方向, 一把斧头在树木与白云 之间闪耀。而小孩 始终相信并为这种声音所吸引, 感受到了某个物种 适时发出四季的信号。 居住在阁楼上的疯爷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 全部都叫狗子,无视 他人纠正,十分搞笑…… 我想,作为旁观者, 这之间,他无非调侃 人人千篇一律, 看似装模作样, 和处在实用事物中的本能。 头脑中想的,熊大熊二 的森林,由一个个 正三角组成。小孩使出 连环计,狗子声嘶力竭: ”我反对!” 像小孩身体里 坐着一个庞大的陪审团, 并拉长声音断喝: “反—对—无—效!” 从心理上先下狗子一城。 金黄大地上,连续三日 人鸟俱无。小孩藏起细软的 身子,暴露出来的脸蛋 并不完整,长着几颗雀斑。 狗子咬住尾巴 越转越快,从里向外看, 狗子应该没有内视反观的能力。 但无论怎么说, 世界弯曲,全景环绕, 目的就是让一些人 在错觉中反过来继续生活。 一些过去的日子依然活在个人化的某个秋天里 像去年一样,至少还要 写一首或两首诗缅怀 与今年秋天比不遑多让 但你必须高于年轻时的姿态 像从朝霞上迎接 归来的故人。别以为这样 就可以得到安慰 秋风一日紧似一日 但我不会按照别人的方式 想出所有不确定因素 说这话时 山中主人也为之一振 正在切生姜腌制咸菜 往坛子里注水 街面上,娃娃闷闷不乐 终于踢响脚下的铁皮罐头盒子 那声音肯定是粗线条的 弯曲而急促,略带不满 我喜欢听白昼 发出的这种声响 绵绵秋雨中 像无线电波长的嘀嗒声 物体与物体自然碰触 一夜未睡 口哨声 一直响到天亮 好像还没有什么 好一点的事情 让人心安 一切正在逐渐消失 北半球的秋天很快就会过去 然后是漫长的冬季 那么多人并不知道 为什么担忧?说起不幸 像搬来半个西太平洋 但令人羞愧的是 天空依然是天空本身 每个人的身体里都隐藏着同一种恐惧 事事都要多加小心 面对面,无论男女 我认识或不认识的 西风吹落一些谷物 每天都要从窗户下面经过 我耐着性子 牵牲口的人大声呵斥 沿途 连续半个月,这种天气变化 被大风拖着 在直觉上开花 风信子早于往年 天空这种丝绸 被大风吹动 倒过来走路,巨人出没 踏落屋顶上的星光 一些表面现象如 石竹花齿细小单薄 披针形叶片交错 展开聚伞状花序与 环绕花柱交织 一群旗鱼飞出海面 也可能带来一些好消息 但多数是一些坏消息 改变极端的精神生活 我无法在这之间做出选择 就像我常常想起一些人 无论他们走多远 也无论他们记不记得 自己是否真实存在过 沿途的图形有方有圆 牧草基本打包完毕 并且像我想的一样 每天会有人从这里离开 在慵常的事物中 我能感受到的 也正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 在北半球奇异的景象中 说话声纷纷亮起了灯光 有关枕头 很早就听说不少枕头的故事 旧时,某某少妇 良人一去不回 私下再为自己 精心缝制一个 面里装满荞麦粒 人一般细高 抱着它睡,即使留不住春夜 春风薄幸 最后被活活捂死…… 我对枕头的体验 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在青冈县大车店 那一只就非同一般 冰凉锃亮没有外套 像个打铁的砧子 窗外寒星四溅 声音自然振聋发聩 杂乱无章之夜 一会儿拉响汽笛 一会儿被压迫的人大声叫喊 一会儿打水饮马 一会儿甜言蜜语 训练灵魂说话的能力 一会儿修补铁皮房盖 一会儿抱起枕头转圈 跳的虽然啥也不是 也不乏有人满嘴跑火车 而上铺正春雷隐隐…… 有关枕头,各类长胳膊长腿的想法 没有人想的和我一样 一片高原上的男女风光 夜话 韩兴贵 ”鬼,你全部出来吧。” “什么意思? 难道刚才看到的 只是她多余的部分? 好你个液体鬼。” “嗯嗯,活着的时候 就特别明亮。” “鬼很快就会散开, 依附白昼,阳光的传单 纷纷撒落下来。” “不仅如此,出于鬼, 有着同一种性状的畏惧或认知, 谁都不想看到, 以人死后的存在感, 最终没有解决。” “对对,灵魂无归宿, 问题满天飞。 说的再具体一些, 她的鬼,如同一颗水银, 化学性质极其稳定。” “长啸梁甫吟, 何时见阳春?” 还是那么多愁哈。 黑夜直接砸下来, 扁平的说话方式, 小张试着卷起对方的话题: “水边有红芍, 山上有老虎。 多年不见, 老虎兄弟你好哇! 呵呵,可否 借你一用?” “他要把你穿在身上, 老虎快跑。” 哇的一声,像加装了 弱音器的小号, 被模拟的完全符合现状, 老虎的处境 与被关在笼子里的 截然相反。 今晚的老虎又大又圆, 有性别的呼唤, 无非是在长满了 桤木松树柳树的 动态空间。 去年的回声 和今年不一样, 像针发出的尖叫。 “该来的早晚会来, 我们都要做准备。” “每到傍晚, 唱独角戏的女子 在甜蜜的空气中忙碌。 脚步慢下来, 与一些点灯的人 正面相遇—— 泉水流过瓦筒, 豆腐又白又嫩。 果真说有一些 穿着条纹的人 走在面前。” 谓言,即便了解 事实的真相, 人们一整天默不作声, 抬头仰视, 每个神灵都抱着 一只恒星的水樽。 “同为哺乳动物, 人首先是动物性, 然后才是其他。 所幸的是, 不受温度控制, 性关系可以放在任何情况下发生, 但不一定 为谁负责。” 老于和老侯凑过来, 谈论起玉泉, 问到窑上的工作, 基本一片灰白。 还说,农村那边的姑娘个个丰腴, 遍地都是, 像剥光叶子的玉米。 他俩颤抖了,坚持以 这样的好天气为标准。 老王上气不接下气, 大意是:正秋高马肥, 从江北买来的那两匹, 第二天又跑了回去。 老杨摘下镜子, 秋霜里的人渐渐融化。 我说,先入为主。 从始至终, 谁也没有分出主次。 来人说,必城隍庙 传来了消息, 神像刚刚请入, 凭空弄丢了脑袋。 秋老虎 秋老虎也是虎 少云的天气 这谁都知道 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又向北抬升 老虎在合唱—— 呜呜呜,哇哇哇 其中这三日就比较炽烈 那几只主动出来 金属的发声尤其刺耳 小朋友问: 都唱的那么凶 会不会没唱完 就把人吃了? 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我想,应该不会 一切都是暂时的 包括我们的大多数同类 一向虎头蛇尾 专门唬人唬钱什么的 这几天里 如同我们一起牙疼 它踱来踱去 忍气吞声 还不如邻居的母老虎 彼此怨恨天天发威 农民伯伯 放下手中的农活 不时抬头擦擦汗 有人在动画片中 乘坐秋老虎回家,一日千里 看不见的车马 被拉出一串白烟 想必早过了 地域意义上的潼关 已逼近十月中旬 3/4拍,一身秋风被花纹感染 又好像突然开挂 打碗花 日夜露宿在外 至今不敢回家 某个寒冷的早晨,等了半天 被比喻成 束蕴请火的那个人 并没出现 即使打碎了整个世界 也不见得 有人在意 然而事实也是如此 从来就没有想过 像人一样丧失信心 更不需要正名 与那些金枝玉叶不一样 甚至没有 一个固定的 精神领地 哪怕真的 从天上来到人间 穿的还是那么少 朝开暮谢 其心何忍? 迟迟不见,在四季 发布的消息里 关于你开花 包括那些 同一形态竞相的场面 被戏弄的日子 忘得一干二净 谄媚也好 献媚也罢 尽在形貌描述 与动作之间 一想就痛 这是成人的做法 正如我们一直都 活在诸多的 生活假象里 远比不上紫茉莉 或碧冬茄 开得那般娇羞 它们的来日 也不是很多 站在夏天洪水的边缘 跳那种危险的舞蹈 看不出 是风儿的肢体在旋转 它只属于一个 未成年的世界 一场游戏结束了。今天像喝醉了酒 我一个人走在午后的阳光里 泉 我要写的泉,并不像印象中的那种 咕嘟咕嘟往上冒 在旁边连接 一小片野地起伏不定 它像一个高度近视的孩子 躲在瓶底般的镜片后面 时不时对着窗口打出两个哈欠 每次去取水时 为了取悦自己 或听见他的说话声 故意把空瓶猛然压入水中 一长串的气泡从水底钻上来 语气神秘 那边的早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谁也说不清楚 已是暮秋天气 松针上挂着一层白霜 太阳一照,变成水滴 下面,在他的头脑中 仿佛睡着一只青蛙从不见醒来 牧羊人和他的妻子 正在乌云下精心挑选羊毛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nchunzx.com/hcwh/15899.html
- 上一篇文章: 走开车去吉林省这11处美丽的地方瞧一瞧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